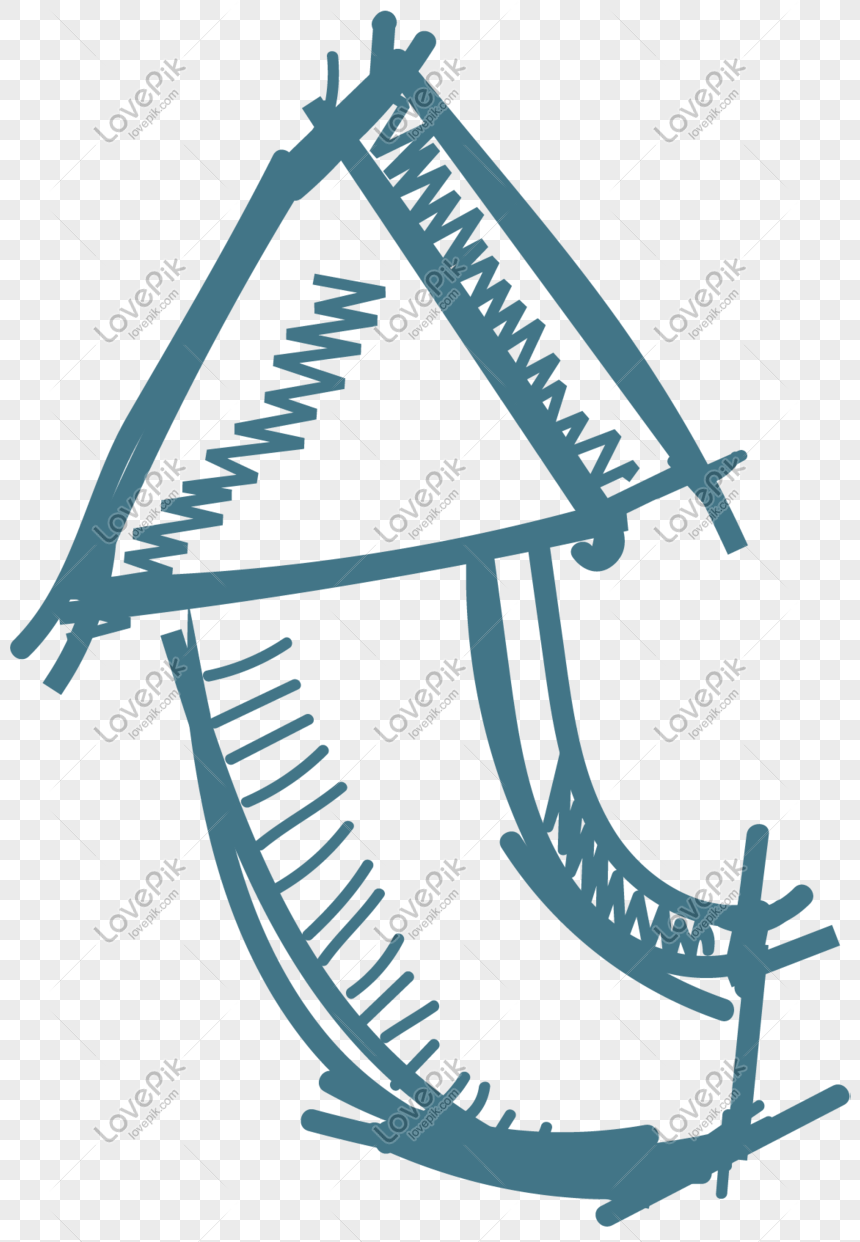都市邊緣的河岸部落
台灣社會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導致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而原住民音傳統農作,狩獵或捕魚等生寄方式難以供給生活所需的現金開銷,陸續從部落遷移至都市謀生,被稱作「都市原住民」。
阿美族都市原住民早期主要從事板模、採礦、遠洋漁業等所謂「最高、最深、又最遠」的底層危險工作,至今也仍大多仰賴體力勞動來營生。不適應資本主義下的儲蓄、積累,使得族人並不容易在都市購屋、租屋,從事營造業的溪洲部落長輩經常戲稱:「我們蓋了都市,卻被都市趕出來。」
是故,三十多年來,北部都市阿美族人受限於經濟條件,總習慣運用自身具備的造屋技巧,依循傳統習慣在都市中打造自己的社區。這些族裔型的都市社區或社群普遍位於都市邊緣角落。
面對迫遷:家是與土地的連結
2007年,台北縣政府「大碧潭再造計劃」,使得位於新店溪畔的阿美族都市原住民部落遭拆遷。
在一系列的抗爭之下,讓都市原住民的居住議題又一次浮上檯面。
現行國家法律的角度觀之,溪畔都市原住民部落確實是不合法的違章建築;然而,若從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法甚至是自然法的角度加以思考,不同法律觀衝突、競合下,先於中華民國政權及法律而存在的阿美族傳統土地使用觀念是否必然「違法」,不無疑問。
而完整的部落環境空間、力求恢復傳統文化的部落組織、固定舉辦的大小活動與傳統祭儀,正是社區團結的來源,緊緊地連繫起溪洲部落裡每一位居民。也就是說,家不只是「房屋」,更是和部落、和土地的連結。若與河岸養育生命的土壤斷裂,部落便不是部落了。
埋石儀式以後,出路在何方?
正因為河岸部落對於族人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都市故鄉而非城鄉遷移中臨時棲身之所。
部落即使遭到怪手無情拆除,居民仍堅持在瓦礫堆上搭帳棚繼續居住,並全體落髮表明捍衛家園到底的決心。
在各種社會團體及記者的大量報導使得原住民議題受到廣泛注目,最終地方政府承諾緩拆。
由於河堤整治,部落仍必須拆除,但縣府同意在原部落後方五百公尺處、水利局的土地上興建由族人自行設計的「溪洲阿美文化生活園區」,待入住後再拆除原部落。
為此,溪洲部落耆老、新店市總頭目萬福全號召族人在2011年3月5日舉行部落埋石儀式,一方面做為部落建立35週年的紀念活動,另一方面,更是團結所有族人一同向外宣告,將在此處安居樂業、永續生根於台北。
黃日華〈溪洲路的心聲〉
碧潭橋的北邊 溪洲路的蕃仔寮
沒有那個Sulafu 那個roma’
Ka-siniadaen
石棉瓦 Ku roma aku’
沒有那柏油路
O haya ka no tao,
Teng-teng han nanay si no suda,kawakucu
kadit-kadit-kadit sanay.